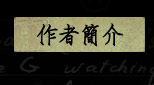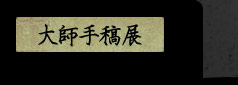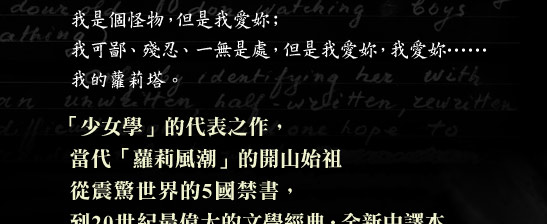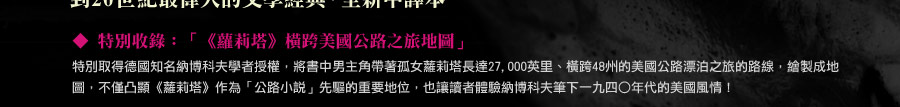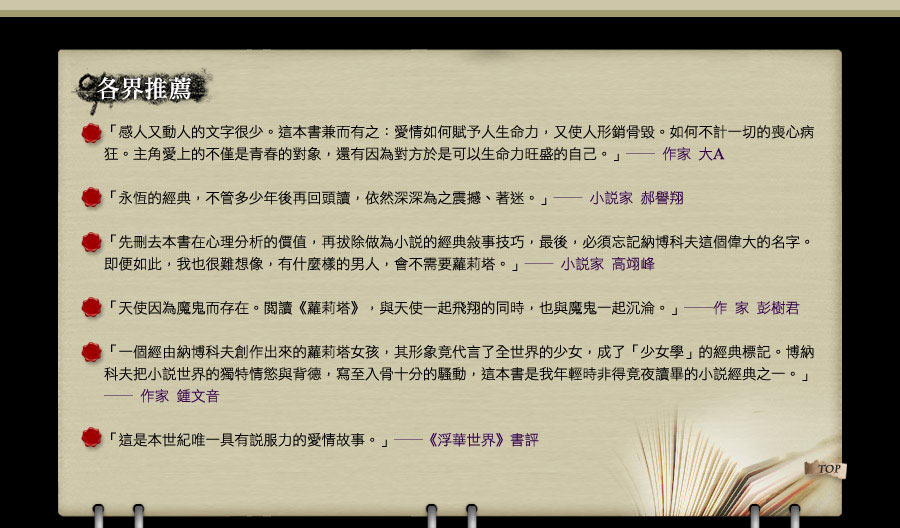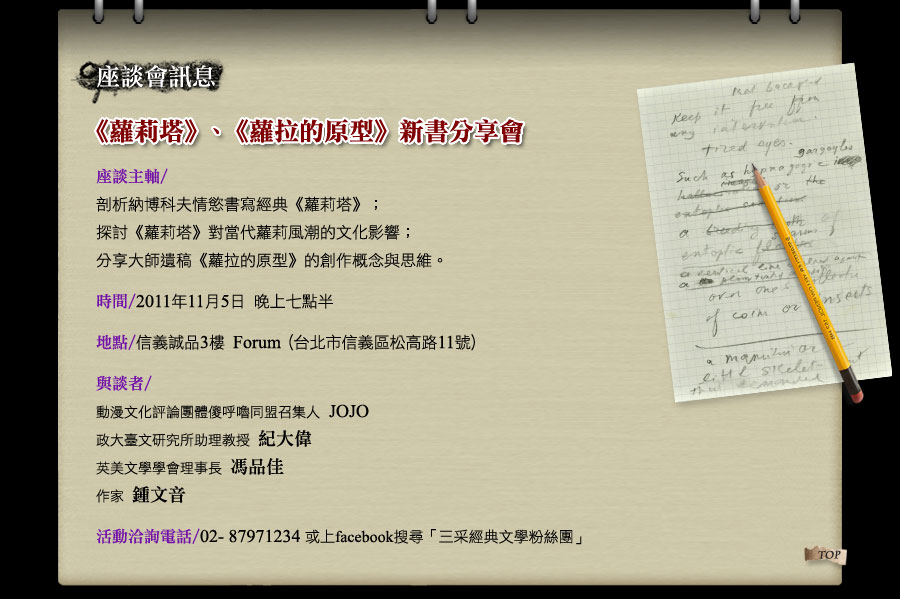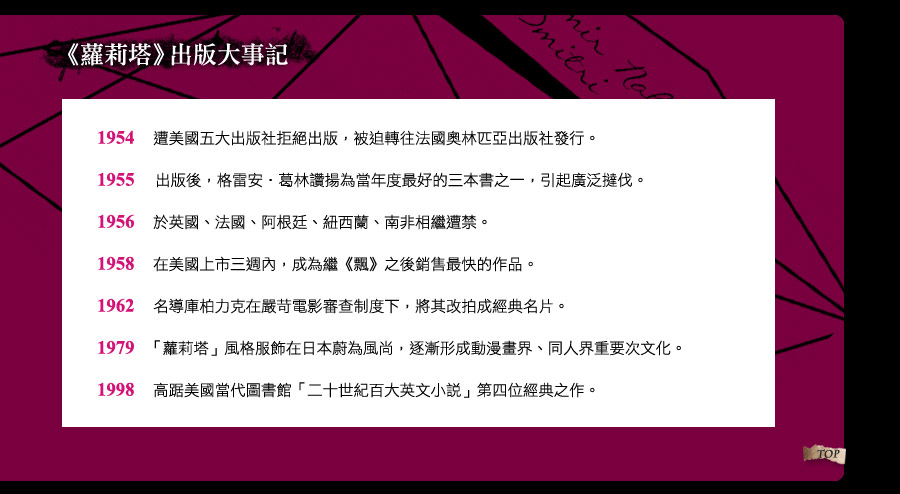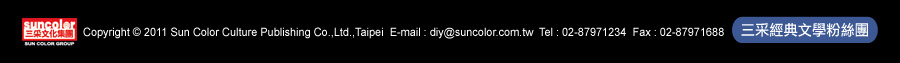1
蘿莉塔,我生命的光芒、我胯下的烈火,我的罪,我的魂。蘿─莉─塔:舌尖從上顎下滑三步,第三步,在牙齒上輕輕點叩。蘿,莉,塔。
清晨時,她是蘿(Lo),平凡無奇的小蘿,四呎十吋高,只穿一隻襪子;身穿寬鬆長褲時,她是蘿拉;在學校她是朵莉(Dolly);正式簽名時她是朵拉芮絲(Dolores)。然而,在我懷抱裡,她永遠都是蘿莉塔。
她有前身嗎?有的,的確有。坦白說,如果某年夏天我沒有愛上最初那名少女,也許根本就不會有「蘿莉塔」的存在。事情發生在一處海濱國度。哦,時間嗎?距離那年夏天蘿莉塔還有多少年才會出生,當時的我就是多少歲。看吧,殺人犯總有別出心裁的寫作風格。
陪審團的女士與先生們,這裡展示的一號證據就連六翼天使們──那受到誤導、單純、擁有高貴羽翼的撒拉弗──見著,都會心生妒羨。請看這團紛亂糾纏的棘刺。
3
安娜貝兒(Annabel)和我一樣,也是異國姻緣的結晶。她有一半英國血統,一半荷蘭血統。在我腦海中,她的容貌明顯比多年前(在我認識蘿莉塔之前)褪色不少。我們的視覺記憶分為兩種:一種是當你睜開雙眼,在大腦的實驗室裡熟練地重塑一幅影像,那時我就可以見到安娜貝兒,伴隨著以下這些平凡的形容詞:「蜜色皮膚」、「細瘦臂膀」、「棕色短髮」、「長長的睫毛」、「大而亮眼的嘴唇」;另一種是只要閉著雙眼就能喚起的影像,暗藏在眼瞼內側深處,那是摯愛面容的視覺複本,客觀且純粹,是天然色彩的小小幽魂(我就是這樣看到我的蘿莉塔)。
那麼讓我來正正經經、拘謹地描述安娜貝兒,就說她是個小我幾個月的可愛女孩。她父母是我姨母的舊識,也和姨母一樣保守無趣。他們住在一棟租來的別墅裡,距離米蘭娜旅館不遠。禿頭的黎伊先生膚色黝黑,富態的黎伊太太總愛抹粉塗脂,其出閣前的閨名叫作凡妮莎.范.涅斯(Vanessa van Ness)。我多麼討厭他們倆!一開始,我和安娜貝兒只是聊些不著邊際的話題,她反覆抓起大把細沙,讓它從指間流泄而下。我們腦子裡關注的念頭和當時一般聰穎的歐洲少年所想的沒什麼兩樣,包括人世間的複雜難解、網球比賽、「無限」的意義,還有唯我論等等,但我不認為這裡面有多少觀點獨到的天才見解。我們都會為柔軟而脆弱的初生小動物感受到強烈的痛楚。將來她想去某個饑饉遍野的亞洲國家當護士,而我要當個名間諜。
我們突然陷入熱戀,愛得瘋狂、笨拙、不顧廉恥且苦悶難當。這裡我應當再加上「絕望」一詞,因為唯有透過實質上吞噬並消化對方的全部靈魂與肉體,那份想要擁有彼此的狂熱才能得到抒解。然而,我們倆卻無法像貧民窟的孩子那般,輕而易舉就能找到交歡的機會。我們一度大膽嘗試在她家花園裡幽會(這件事容後再述)。在那之後,我們唯一的私人空間就是人來人往的海灘,待在大人們聽不見我們談話、卻看得到我們身影的幾呎外。在那片柔軟的沙灘上,我們會懶洋洋地躺臥著,當令人顫抖的情慾來襲時,便利用每個空間上和時間上的天賜良機,偷偷碰觸對方。她半掩在沙子裡的手會偷偷向我這邊挪移,那些修長的褐色手指夢遊般愈靠愈近,她乳白光澤的膝頭也會步履謹慎地朝我展開漫長旅程。偶爾,幼小的孩童會碰巧來到我們身邊,以沙築出臨時的堡壘,讓我們得以在充分掩護下吸吮對方帶有鹹味的嘴唇。這些意猶未盡的碰觸,使得我們健全而不諳人事的年輕身軀彷彿被激情的烈火折磨著,即使在沁涼的湛藍海水裡緊緊攫住彼此,也無法平息。
成年後我浪跡天涯,旅途中遺失不少珍貴物品,其中有一張我姨母拍攝的快照。照片裡的人圍坐在露天咖啡館的圓桌旁,有安娜貝兒和她父母,還有那年夏天追求過我姨母的庫帕博士。庫帕博士年長穩重,瘸著一條腿。安娜貝兒那張照片拍得不好,因為當時她正好在低頭吃她的巧克力冰淇淋,她美麗的身影漸層般消失在日間的朦朧光影中,唯一可辨識的是她裸露的瘦削肩膀和頭髮的分線(根據我對那張照片的記憶);而我──稍稍遠離眾人獨坐──在照片中的影像異常清晰:一個穿著深色運動上衣和剪裁得宜的白色短褲、悶悶不樂且眉頭深鎖的男孩,交叉雙腿坐著,目光看向別處。拍那張照片的時間正是那個關鍵性夏天我們相處的最後一天,就在我和安娜貝兒第二度──也是最後一次──試圖反抗命運的幾分鐘前。我們捏造了極為薄弱的託辭(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所以我們都不在乎),從咖啡館溜到海邊,找到一處無人沙灘。在那裡,幾塊緋紅岩石灑下了暗紫色的陰影,看上去彷彿一處洞穴。我們急切貪婪地相互愛撫,唯有別人遺失的一副墨鏡充當我們的見證。當我跪在地上,即將占有心上人那一刻,突然來了兩名蓄著鬍鬚的泳客,是老漁夫和他弟弟。他們一邊從海裡走上岸,一邊叫喊些下流話語鼓舞我們。四個月後安娜貝兒在希臘科孚島病故,死於斑疹傷寒。
4
我再三檢視這些悲慘往事,不斷自問,我的生命是不是從那個陽光燦爛的遙遠夏季開始撕裂;或者,我對那女孩的極度渴望只是某種天生怪癖的初次體現?每當我試圖分析自己的渴盼、動機、行為等等,總會在追憶往事時耽溺於想像中,任由想像力為執行分析任務的大腦提供無窮無盡的可能性,以致大腦具體思考出來的人生路途分岔再分岔,不會踏上如同我的過去那般令人發狂的複雜人生。然而,我仍深信,基於某種神力與宿命,蘿莉塔事件是從安娜貝兒開始的。
我更知道安娜貝兒的死強化了那個噩夢般夏天的挫折感,從而造成永久性的障礙,使我的青年時期一片淒寒,無法在戀情上有任何進展。我與安娜貝兒的精神與肉體完美交融,這點時下那些實事求是、粗俗、思想標準化的年輕人恐怕永遠難以理解。安娜貝兒死去很久以後,我還能感覺她的思緒穿過我腦海。早在我們相遇之前,我們就做過相同的夢。我們談過各種話題,發現彼此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度。某一年(一九一九年)的六月,當時我們各自居住在相去甚遠的兩個國度,我家和她家竟同時有隻鼓動雙翼的迷途金絲雀闖入。噢,蘿莉塔,但願妳也如此愛戀我!
我還沒描述和安娜貝兒之間的第一次失敗行動,此時就用它來總結「安娜貝兒時期」。有一天晚上,她成功地脫離家人的嚴密監控。我們去到她家別墅後方,在含羞草叢那怯生生的細長枝葉中找到一處已然崩壞、可供休憩的低矮石牆。透過昏黯夜色與柔嫩樹枝,我們可以瞧見被燈光照亮的窗玻璃上頭的阿拉伯風格圖案。窗玻璃經過敏銳記憶的彩筆潤飾,如今想來似乎頗像紙牌──或許是因為當時我們的「敵方」正忙於一場橋牌遊戲的緣故吧。我親吻她微啟的唇角和暖熱的耳垂時,她渾身顫抖抽搐。點點星辰在我們頭頂上方細長的樹葉剪影中閃著微光。夜空一片明亮,看上去就跟遮掩在輕薄連衣裙底下的她一般赤裸。我看到她的面容出現在天空中,異常明顯,彷彿散發著微弱光輝。她的雙腿,她那可愛而活躍的雙腿並沒有靠得很近。當我的手找到目標,她那童稚的面容出現一種彷彿置身夢境的奇妙神情:半是愉悅,半是痛楚。她坐得比我稍高一些,每當她陷入自我的狂喜境界、想要親吻我時,她的頭會以一種處於昏睡狀態、柔軟而低垂的姿勢,近乎悲傷地稍稍往下彎。她裸露的雙膝緊緊壓制我的腕關節,然後又鬆開來。她顫抖的嘴彷彿飲用了某種神祕藥水而扭曲變形,一邊吸氣、一邊發出嘶嘶聲響,朝我的臉龐貼近。她會先用乾燥的嘴唇草草地在我唇上廝磨,藉此緩解思念的苦楚,而後我的愛人會緊張地甩甩頭髮,移開她的臉,接著再度悄悄靠過來,讓我盡情享受她的雙唇。而我已經準備好要向她奉獻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心、我的喉和我的內臟,慷慨大方地把我熱情的權杖交到她笨拙的手掌裡。
記憶中有一股爽身粉氣味──我想那是她從她母親的西班牙女僕那裡偷來的──甜美、卑微的麝香調香水。那股氣味與她身上那股餅乾香混雜一氣,我的感官鼓脹,瀕臨爆發邊緣。附近灌木叢忽然出現動靜,遏止了我的熱情。我們連忙分開,血脈賁張又痛苦地張望查看。應該是路過的覓食貓兒。就在那時,屋裡傳來她母親呼喚她的聲音,聲調漸次升高,而庫帕博士則一瘸一拐、拖著沉重步伐走進花園。那叢含羞草、那黯淡的星辰,那股刺痛與烈火、那些甘露和痛楚,至今都還跟隨著我。那個四肢經過海灘陽光洗禮、有著熾熱舌頭的小女孩從此縈繞在我心靈。直到二十四年後,我終於讓她在另一個人身上重生,才得以打破她的魔咒。
5
如今回首往事,我年輕的歲月有如反覆出現的蒼白碎片,亂紛紛地離我遠去,就像火車旅客望向車廂外時會見到的景象:車行過處,被棄置的衛生紙有如清晨的暴風雪般,盤旋飛舞。在與女性的肌膚之親方面,我務實、譏誚又活躍。在倫敦和巴黎就讀大學期間,煙花女子就能滿足我的需求。我的學業密集又沉重,成績並不特別顯著。一開始,我跟眾多資質平庸的青年一樣,希望在精神病學領域拿個學位,可惜我的資質顯然比平庸更平庸,我飽受壓力,心神耗弱,醫師對我下達最後通牒,我只得轉而攻讀英國文學。那個圈子裡有許多不得志的詩人,最後都變成身穿花呢外套、叼著煙斗的教師。巴黎很適合我,我在那裡和一些客居當地的外國人談論俄國電影;在「雙叟」咖啡館與同性戀者共席交談;在默默無聞的刊物上發表冗長乏味的文章。
我寫過一篇題為〈談濟慈致班傑明.貝利書信中的普魯斯特議題〉的論文,遭到六、七名讀過的學者訕笑。我為一家著名的出版商編纂《英詩簡史》,而後又著手為說英語的學生整理法國文學導讀(收錄跟同時期英國作家的比較),這項工作讓我在一九四○年代保持忙碌。當我被捕時,最後一冊即將付梓。我在奧圖耶找到一分差事,指導一群成人學習英語,之後一所男子學校連續幾年冬天聘任我。偶爾我會利用我與某些社工人員和精神科醫師的交情,隨同他們造訪各個機構,比如孤兒院或感化院。在那些地方,我得以盡情欣賞那些有著濃密睫毛、令我想起某位夢中人的蒼白少女,絲毫不必擔心遭受責難。
此刻我想要闡述以下觀點:在那些被迷惑的旅人眼中,某些介於九歲到十四歲這個年齡層的少女顯得比實際年齡大兩倍以上。從外顯特質判斷,她們不是凡人,而是具有魔性的仙女。我提議將這群特別的人兒命名為「小魔女」(nymphets)。
請特別注意,我以時間條件取代了空間條件。事實上,我希望讀者把「九」和「十四」視為一座魔幻島嶼的邊界──光可鑑人的海灘與玫瑰色的岩石。那座島嶼上住著我那些小魔女,周邊圍繞著渺無邊際、迷霧氤氳的大海。然而,那個年齡層裡的少女個個都是小魔女嗎?當然不是,否則我們這些孤獨的旅人、魔女的行家與崇拜者早就精神錯亂了。美貌不是判別的標準,而粗野的舉止──套某些人的話來說──同樣也無法減損她們身上的某種神祕性:那種精靈般的優雅,那種飄忽、難以捉摸、詭譎多變、令人魂飛魄散的潛藏魅力,讓小魔女們與同齡女孩殊異。比起蘿莉塔和她的同類玩樂其間、那座跳脫時間感的虛幻島嶼,其她女孩對於同時代空間上的現象世界有著更高度的依賴。比起她們頗為平庸的同輩,正牌小魔女的人數在同齡女孩之中少得出奇。那些平庸女孩我們姑且稱之為「善良」、「可愛」,甚至「甜美」與「嫵媚」。她們普通、豐腴、毫無特色、膚觸冰冷。這些肚腹微凸、梳著辮子、本質上為人類的女孩們,將來也許會(也許不會)出落成標致的大美人(看看那些穿戴黑色長襪和小白帽的醜小鴨們蛻變成螢幕上的絕色女明星)。若是要求一名普通男人從女學生或女童軍的團體照中挑選出最漂亮的一個,身居其間的小魔女往往未必中選。非得是個藝術家或瘋子,或是長期鬰鬰寡歡、胯下有團熱氣蒸騰的毒液,而敏感部位的旺盛慾火永恆燃燒著(唉,你得耗費多少苦心畏縮隱藏!),只有這樣的人才能一眼就從健全孩童之間辨識出那個致命的小惡魔,辨識出那些難以言喻的特徵──頰骨上隱約浮現的、貓一般的輪廓;布滿細毛的修長四肢。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其他諸多指標,但絕望、羞恥和柔情的淚水不容我在此逐項列舉。她就站在那裡,旁人認不出來,她對自身的驚人魔力也蒙昧無知。
更進一步來說,既然時間在這件事上頭扮演如此神奇的角色,那麼有意探究的人就不應該對其中涉及的年齡差距大驚小怪。我認為,男方至少要比女方年長十歲以上,通常要大上三十歲到四十歲,更有少數相差九十歲的已知案例。唯有如此,小魔女的魔咒才能迷惑男方。那只是焦點調整的問題:讓心靈之眼興沖沖想去跨越那段距離,且讓理性的心以一種扭曲的喜悅看待那種對比。當我還是個孩子,而我的安娜貝兒也是個孩子時,她在我眼中並不是小魔女。在同一座時間的魔幻島嶼上,我自己也是個小魔童,與她身分相當。可是時至今日,經過二十九年以後,在一九五二年的九月,我想我能夠清楚分辨,她就是我生命中那第一個宿命的小精靈。我們以一種早熟的情愛相互眷戀,那種愛極其熾烈,往往足以毀滅成年人的生命。當時我是個健壯的少年,所以我存活下來,只是毒藥還留置在傷口裡,傷口從未癒合。很快的,我發現自己長大成人,而周遭的社會容許二十五歲的男子追求十六歲女子,卻不容許他愛戀十二歲少女。
……
10
出院後,我開始尋尋覓覓,想在新英格蘭郊區或某些恬靜的小鎮(有著榆樹和白色教堂)找個地方停留一整個夏季,運用我過去累積下來、滿滿一整箱的筆記辛勤著作,偶爾在附近的湖裡游泳。我對工作再度提起興致。我指的是學術上的工作,至於我在姨父留下的香水事業的參與度,到那時節已經被縮減到最低程度。姨父以前的一名下屬──來自有名望的家族──提議我到他經濟拮据的表親(已退休的麥庫先生和他妻子)家暫住幾個月。麥庫夫婦有意出租住家二樓,原本靜靜居住在那裡的姨母新近才過世。他說他們有兩個小女兒,其中一個還是小嬰兒,另一個十二歲,有個美麗花園,附近有風景宜人的湖泊。我說這個主意完美至極。
我跟那些人以書信聯絡,告訴他們我生活習慣很好。我在火車上過了美妙的一夜,想像著那個不知名的小魔女,我即將以法語指導她,以韓伯特語撫弄她。我拿著新添購的昂貴提袋在那個小車站下車時,沒人來接我,打電話也無人回應。最後,心煩意亂的麥庫先生渾身溼淋淋地來到粉紅嫩綠的蘭斯岱爾唯一一家旅館,告訴我他家被一把無情火燒毀──可能是同一天夜裡在我血管裡燃燒到天明的那把火所致。麥庫先生說,他家人不得不暫時到他擁有的一座農場棲身,把車子也開去了。不過他妻子有個人品很高尚的朋友,就是住在羅恩街三百四十二號的海茲太太,願意把房子租給我。海茲太太對門的女士把她的豪華禮車借給麥庫先生使用。那部車款式非常古典,方形車頂,司機是一名開朗的黑人。既然我來此的唯一原因已經消失,剛剛那些安排顯得非常可笑。好吧,他的房子得重新修建,那又怎樣?他沒有投保足額火險嗎?我既氣惱、失望又煩悶。可是身為有教養的歐洲人,我不能拒絕搭乘那部靈車去到羅恩街,因為我覺得如果不照辦,麥庫先生恐怕要想出更複雜的辦法來擺脫我。我目送他跑步離開,而我的司機一面搖頭、一面低聲咯咯笑。途中我暗自發誓,無論如何決計不要留在蘭斯岱爾,當天就要飛往百慕達(the Bermudas)、巴哈馬(the Bahamas)或巴雷茲(the Blazes,即地獄),在那些亮麗沙灘可能嚐到的甜美滋味曾經在我脊髓裡流淌好些時日,麥庫先生表親的好意讓我那一連串思緒中途轉向,只是他的好意如今看來是多此一舉。
說到急轉彎:我們轉進羅恩街時,險些壓過一隻不安於室的鄉下蠢狗(那種會躺在路上等車子經過的狗)。海茲家出現在前方不遠處,一棟白色結構的醜陋屋舍,骯髒又老舊,白色牆面已經變灰──就是那種浴缸水龍頭肯定接了一條橡皮水管,好替代蓮蓬頭的屋子。我給了司機小費,希望他會立刻開走,方便我神不知鬼不覺地轉身回到旅館拿行李。但司機只是越過馬路走到對街,那裡有個老婦人在門廊上呼喊他。我能怎麼辦?只得按門鈴。
一名黑人女僕讓我進門,她把我留在進門處,趕緊衝進廚房,說她在爐子上燒的菜可不能燒焦。
前廳有些裝飾品,包括一組門鈴、不知是什麼玩意兒的白眼木雕品(顯然是來自墨西哥的商業化藝品),還有附庸風雅的中產階級喜愛的通俗裝飾畫──梵谷的《吉諾克夫人》。右邊有一扇半掩的門,露出裡面的客廳。客廳角落的櫃子裡擺了更多墨西哥廢物,牆邊擺著一座條紋圖案沙發。走道盡頭有座樓梯。我站在原地,邊看邊抹著眉頭的汗水(這時我才發現室外有多熱),忽然看到某件物品,那是一顆放在橡木櫃上、灰灰舊舊的網球。上方樓梯轉彎處傳來海茲太太低沉的嗓音。她靠在欄杆上,用抑揚頓挫的聲調問道:「是韓伯特先生嗎?」點點煙灰從天而降。此刻,那位女士本尊──涼鞋、紫紅色寬鬆長褲、黃色絲質上衣、方形臉,依序登場──走下樓梯,食指還在彈著煙灰。
我想我最好在此描述她,早早把事情了結。這位可憐的女士三十多歲,前額發亮、修過眉毛,相貌平平,尚稱嫵媚,勉強可以說是少了點風韻的瑪琳娜.狄崔西。她拍拍銅棕色髮髻,領我進入客廳。我們在那兒閒聊一分鐘,談了麥庫先生家的火災,以及住在蘭斯岱爾真是三生有幸。她那海綠色的雙眼分得很開,用一種有趣的方式把人全身上下打量一遍,卻是小心翼翼地避開你的視線。她笑起來只有一邊眉毛滑稽地抖動一下,坐在沙發上說話時趁便舒展四肢。她手上的煙不時衝向三只煙灰缸和附近的炭爐(裡面躺著一個褐色蘋果核)。之後她又會靠回沙發,把一隻腳縮在屁股底下。她就是那種談吐優雅的女人,但那些辭藻反應出讀書會或橋牌社(或其他死氣沉沉的俗物)的薰陶,卻顯現不出她的靈魂。那種女人毫無幽默感。她其實對適於在客廳裡談論的十來個話題毫不感興趣,卻會挑剔談話時的規則,而在那些規則的燦爛玻璃紙下顯而易見的是惱人的挫折感。我心裡再清楚不過,萬一我成了她的房客,她馬上會展開行動,依照她心目中房東房客該有的相處模式,有條有理地進行規範,而我也會再度捲入那種我再熟悉不過的繁瑣事務之中。
我當然不可能搬進這裡。這屋子裡破爛雜誌隨處可見,既有所謂的「實用現代家具」,更有東倒西歪的破舊搖椅、外加擺放故障枱燈的搖晃茶几,無疑是喜劇與悲劇的恐怖結合。待在這裡我無論如何開心不起來。我被帶上樓,向左轉,走進「我的」房間。我用徹底排斥的偏見眼光檢視房間,卻在「我的」床頭上方看到雷內.普林湼特(René Prinet)的畫作《克羅采奏鳴曲》(Kreutzer Sonata)。女僕的房間在她口中成了「半套工作室」!我這位興沖沖的女主人要求的房租伙食費低得不合理,顯然是不祥的前兆。我一邊假裝考慮,一邊堅定地告訴自己:立刻離開這間屋子。
然而,歐洲的舊社會禮儀逼得我不得不繼續這場磨難。我們走過樓梯間,來到屋子另一側(那是「我和小蘿的房間」──小蘿想必是那位女僕)。當這位房客情郎──一位非常挑剔的男子──獲許參觀唯一的浴室,幾乎藏不住一陣寒顫。浴室是個小小的長方形空間,座落在樓梯間與「小蘿」臥房之間。裡面有些溼衣物鬆垮垮地垂掛在曖昧的浴缸(裡面有根扭成問號的頭髮)上方。預料中的橡皮蛇果然盤繞在那裡,而它的配件──粉紅色的套子──則是怯生生地包覆著馬桶蓋。
「看來您不怎麼滿意,」那位女士說話時把手搭在我衣袖上。她的神態混合了沉著的坦率──應該是所謂的「鎮定」的過度表現──與害羞和悲傷,以致她那種不帶情感的遣詞用字,顯得跟教「演說法」的教授的音調一樣不自然。「我承認,這屋子確實不夠整齊,」這位大勢已去的女士又說,「可是我跟您保證〔她瞧著我的嘴唇〕,您可以住得很舒適,非常舒適,真的。我帶您參觀花園。」(最後一句話聽起來比較愉快,聲音頗為迷人)。
我不情願地隨她回到樓下,穿過走道盡頭的廚房。那是在房子的右側,跟用餐室、客廳同一邊,而「我的」房間在左側,底下只有車庫。廚房裡,黑人女僕──胖嘟嘟的年輕女子──一邊從通往後廊的門把上取下她那發亮的黑色大皮包、一邊說道:「海茲太太,我先走了。」「好,露易絲!」海茲太太嘆著氣回答。「我星期五再跟妳談。」我們經過餐具櫃,轉進用餐室。用餐室和我們欣賞過的客廳並排。我注意到地板上有一只白襪子,海茲太太不悅地哼了一聲、邊走邊彎腰將它拾起,扔進餐具櫃旁的櫃子裡。我們草草鑑賞了紅木餐桌。餐桌正中央擺著水果盤,裡面空無一物,只有一個依然閃閃發亮的洋李果核。我翻找口袋裡的時刻表,偷偷拿出來查閱最近一班火車的時間。我還跟在海茲太太身後走過用餐室,前方突然出現一片翠綠──「這是我們的花園廣場!」海茲太太喊道。然後,一股湛藍浪潮無預警地從我心底湧起。沐浴在日光下的墊子上,有個跪在地上的半裸少女,正雙膝著地轉過身來。那是我的蔚藍海岸情人,躲在墨鏡後方盯著我瞧。
那是同一個孩子──同樣嬌弱的蜜色肩膀、同樣絲綢般柔滑的裸背、同樣的栗色頭髮。她胸前繫著一條黑色圓點大方巾,藏起我在不朽的那一日撫弄過的少女乳房。方巾雖然遮擋了我日漸衰老的痴狂目光,卻擋不住我年輕記憶的凝視。我宛如童話故事裡某位小公主的神仙保姆,小公主失蹤、被綁架,被發現時身上披掛著吉普賽人的襤褸衣衫,衣衫底下的裸體則對著國王和他的獵犬微笑。我認出她側身那顆深褐色的痣。我又喜又懼(國王喜極而泣;號角響徹雲宵;保姆陶醉了)。再次看到她那微凹的可愛肚腹,我下行的嘴曾在那兒短暫停留;還有那稚嫩的臀,我在那兒吻過她的短褲鬆緊帶留下的細齒狀痕跡,就在瘋狂且不朽的最後一天、在我與安娜貝兒的「緋紅岩石」叢後方。在那之後我所度過的二十五年時光慢慢縮減,最後剩下一丁點悸動,從此消逝。
我發覺很難強而有力地解釋那種電光乍閃、那份震撼顫慄、那種激情相認的衝擊。在陽光燦爛的那一刻,我披著成人的偽裝(幻想世界裡英挺偉岸的帥氣男子)走過她身旁,視線滑過那跪著的孩子(她的眼皮在嚴肅的墨鏡上方眨呀眨地──她就是即將治療我所有傷痛的「醫生閣下」)全身。我真空的靈魂努力吸取她那鮮明美貌的全部細節,然後拿來對照我已故新娘的特徵。當然,再過不久,她,這位新人,這個蘿莉塔,我的蘿莉塔,就會完全取代她的原型。我只想強調,蘿莉塔的出現,正是我過去的痛苦歲月裡那「海濱國度」的致命結果。兩起事件之間的一切都只是摸索與碰撞,是歡愉的虛妄假象。她們之間所有的共同特徵讓她們合而為一。
然而,我並不心存幻想。我猜我的法官會把這一切看成是偏好青澀果子的變態瘋漢上演的一場默劇。基本上,我不在乎。我只知道,當我和那個姓海茲的女人走下台階,進入那令人窒息的花園時,我的雙膝像是映在水面漣漪上波動的倒影,而我的唇乾燥似砂礫。然後……
「那是我的小蘿,」她說,「這些是我的百合花。」
「嗯,」我說,「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