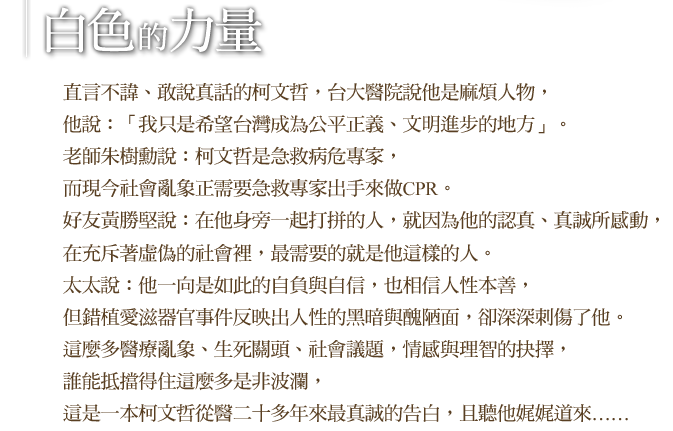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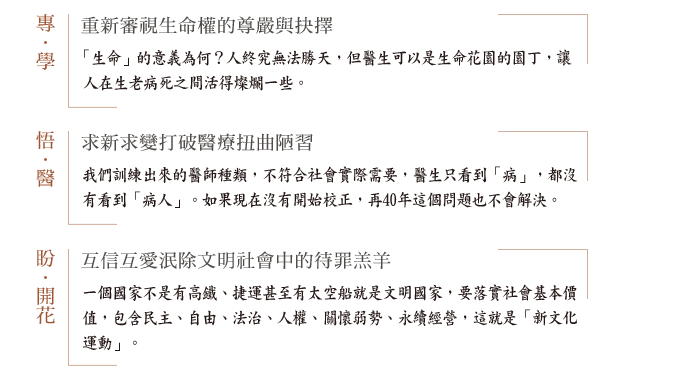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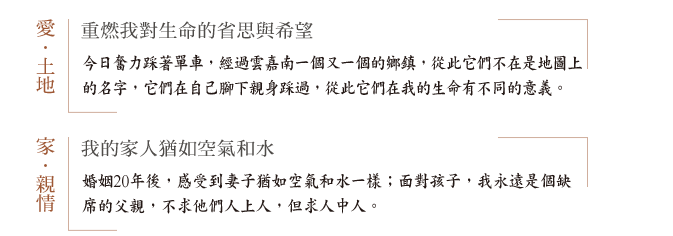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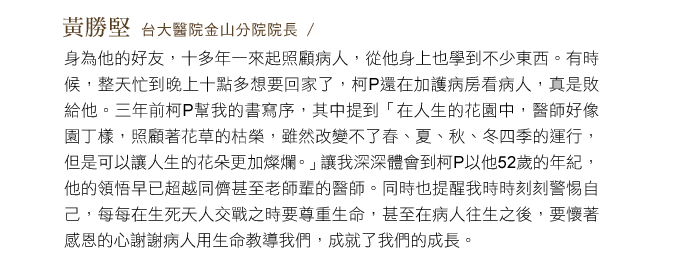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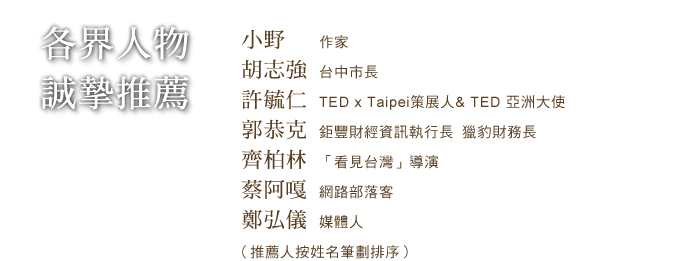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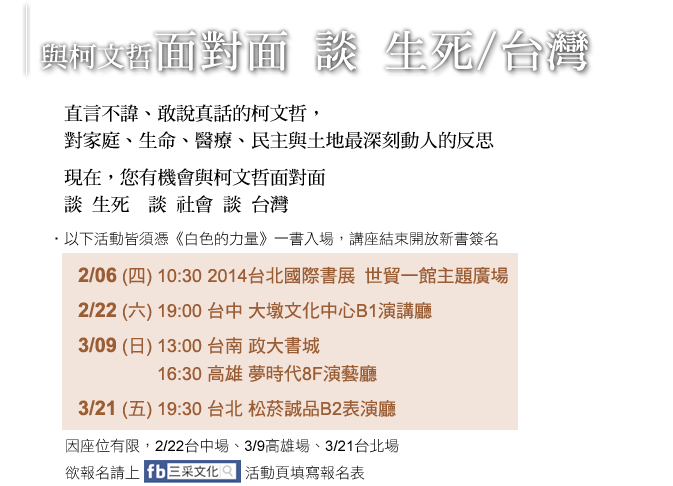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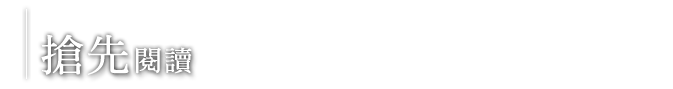 |
怎樣算「活著」,「死亡」又是什麼?
我對這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反問:怎樣才算是「活著」?也就是如何才算是有「生命」?葉克膜的出現,讓生死的界線更加模糊,因為葉克膜可以取代心肺功能,在管路上再架設CAVH((continuous arterio-venous henofiltration)可取代腎臟功能,定期大量的血漿交換可取代肝臟功能。當一個人主要的器官功能全部被機器取代,躺在床上,全身被管線圍繞動彈不得,但是生命徵象,包括心電圖,血壓卻是穩定的,這個人算是活著嗎?
曾有26歲男性,因為溺水,造成嚴重肺衰竭,在使用葉克膜一一七天之後,完全康復出院。但也有肺臟移植一年半之後,慢性排斥引發呼吸衰竭,在使用葉克膜六個月之後,因為敗血症而死亡。如果有機會回復,葉克膜治療伴隨的痛苦,我們可視為救治的代價。但如果確定無救治機會,則長期葉克膜之使用,到底是延長生命?還是延長死亡過程?
有人認為所謂生命就是死亡過程,因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們就往死亡接近,因此整個生命都是「倒數」的,每過一分鐘,就是生命少了一分鐘。因此延長生命就是額外賺到的,盡力去延長生命是合理的。關於此點,我並無反駁的意思,但是QALY(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之概念,QALY= quality × time,如果生活品質(quality)<0,那麼即使時間(time)再怎麼延長,計算出來仍是負值,也就是「生不如死」。
換句話說延長的生命,也要有一定的品質,才值得延長。但是這個問題的倫理困境在於品質(life quality)由誰來認定?例如以葉克膜維持生命的昏迷病人,也確定無恢復之可能,此時的「品質」由誰認定?尤其當病人自己已昏迷無法做決定,家屬徬徨不知所措,醫師以安寧緩和條例第七條為理由:「非病人本人不得決定撤除維生系統」,而讓葉克膜一直使用下去,健保局則是無言的付錢(或許事後會有不確定的健保核刪),似乎此時唯一確定的受益者是販賣葉克膜的廠商。
葉克膜讓生死的界線變得模糊,逼迫我們正視生命的意義為何?生命的品質如何量化?由誰決定?決定的人是否就可以指使醫師提供葉克膜的治療?所有這些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綜合以上所言,似乎我們提出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但是「生命」的意義為何?我個人的見解,追求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就是說「生命」只是一個過程,並沒有確定的目的。因為單一生命終將毀滅,因此如何說它有何目的?總不能說存在之目的在於其結束。因此生命只是一個過程,在過程中實踐了生命之意義。 倫理之困境將永遠存在!葉克膜固然救活了很多以前無法救治之病人,將生死之間的界線,往死亡方面又推進了不少,使「生」的範圍更大了。但是界線還是存在,甚至界線本身變寬了,生死夾雜,也產生新的倫理困境。
有一天我體悟了,醫生無法改變生老病死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我自從專職外科加護病房工作以後,承蒙當年的上司朱樹勳教授大力支持,外科重症是整個台大外科的重點,人力、物力之支援皆是第一優先。因此器官移植、葉克膜、人工肝臟、各種透析技術、各種人工維生系統,不過幾年之光景,就追上世界水準。曾有一段時間,台大醫院的記者招待會,和我們外科加護病房有關的就占一半之多。當時真覺得「人定勝天,科技萬能」,心中好不得意。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無奈科技終究有其極限,胡夫人邵曉鈴、星星王子、……固然是令人欣喜的成功案例,但也有不少救不活也死不去的,甚至可說是「灌流良好的屍體」,面對焦慮的家屬,狐疑的同事,甚至自己站在病人的床邊,挫折的無奈竟然掩蓋了所有過去的欣喜,變成揮之不去的夢魘。
眾裏尋它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
慢慢的,終於了解人生有「生老病死」,就如氣候有「春夏秋冬」。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作焉」。終於領悟醫師就是醫師,其目的只是替人世減少苦痛,不管是身體的或精神的。人生花園之中,醫師只不過是一名園丁吧!我們不能改變「春夏秋冬」的循環運行,卻可盡力讓人生的花朵更加燦爛。有時雖是園丁照顧花草,有時反而是花草的枯榮在度化園丁。
我已經是怪醫秦博士了,臺灣最厲害的醫生,這樣講好像太臭屁了,有一天突然就想到,醫師只是讓人在生老病死之間活得好看一點,慢慢的從科技回歸到人性,所以後來慢慢又看到病人,我有好多年的時間沒有看到病人,從科技回到人生。
憶起生死兩相安,再無遺憾
曾有一位大老闆,在事業正盛時,罹患克雷氏桿菌肝膿瘍,開刀引流後,卻引發嚴重敗血症併發急性呼吸窘迫症,最後被迫使用葉克膜維持生命。病況最嚴重時,呼吸器每次通氣量不到一百西西,後來更併發急性腎衰竭,在葉克膜管路上再架設洗腎的管路。
當年正好國際外科醫學會在台北舉行,葉克膜祖師巴特雷醫師(Dr. Bartlett)也受邀來台與會演講,順道拜訪台大醫院時,帶他參觀加護病房,結果他在此病人床邊站了一個小時,東看西看直說:“wonderful!”。後來他到處跟人家說,台大的葉克膜是世界最強的團隊之一。
經過五十五天的漫長葉克膜治療,終於把病人搶救回來,對醫療團隊而言,與其說是高興不如說是得意。後來轉到普通病房後,突然有一天病人有急性盲腸炎,當時只想真是禍不單行,不過還是立刻安排緊急手術,術後開刀醫師告訴我,闌尾看起來發炎不嚴重,倒是盲腸壁感覺較厚。反正開完刀後一切順利,也就沒有追究了。
出院後不到半年,在一次例行胸部X光片檢查發現有一顆腫瘤,細針穿刺檢查之病理報告赫然是淋巴瘤。電腦斷層發現腫瘤已沿著主動脈蔓延到整個中膈腔。至此回想,才知道原來一開始是腸胃道淋巴瘤,造成腸黏膜潰瘍,細菌藉此侵入引發細菌性肝膿瘍以及後續的一連串事件,後來的急性闌尾炎,只是局部的併發症而已。
知道真相後,原有的葉克膜治療成功的喜悅一下子被澆息,當然也替病人找了最好的醫師、最好的藥物,初期治療效果也不錯,但腫瘤一再的復發,最後望著胸部X光片,看著腫瘤一天一天的變大,變成我最大的痛苦。
害怕病人問我:「有無其他治療方法?」
痛恨自己含糊回答:「我再想想。」而事實上,已無法再想。
有一天,病人突然對我說:「我這一關死定了,我很謝謝你的努力,你就不要再有壓力了。」我們兩人無言相望半响。
後來我忙完一天的事,晚上十一點多才去看這個病人,通常家屬也回家了,空盪的15C單人病房變成醫師和病人的午夜會談。
這麼多年過去了,治療過程的欣喜、挫折,都忘記了。唯一還有記憶的,卻是兩人午夜聊天,甚至兩人的相對無言,最後這一段日子,因兩人的互信互諒,我們做到了生死兩相安,再無遺憾。他走得很平靜,從此我知道醫生在診斷、開刀、藥物治療以外,還有一些可做的事,甚至什麼事都沒做的相對無言之中,也有醫師的價值在其中。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
大四剛當見習醫師時,初次穿上醫師袍,要去看病人之前,都會先問護士姐姐,打聽一下病人來自哪裡?作什麼工作?有那些主要親屬?那時候,看到的病人都是一個完整的病人,有七情六慾,是家中的一員,社會中的一分子。我不但看到病人,也看到床邊的家屬。
後來醫術日益精進,擠身名醫之列,看到轉診紀錄,抽血數據瞄一眼,系列心電圖逐張看過去,床上的病人都沒有看到,已脫口而出:「急性心肌炎」,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只看到「器官」,沒看到「人」,只看到「病」,沒看到「病人」,更不用說旁邊的家屬。
直到最近才又重新看到「病人」了,不再只是數據、超音波、病理報告的組合。而是一個有喜怒哀樂,在家庭、在社會中牽扯不清的一個人。